清末的士绅与武汉警政
时间:2024-01-21 11:30 作者:创始人 点击:[7]
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国家权力对地方事务的干涉相对减弱。地方精英扮演了各种活跃的角色,他们的经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持续扩张。在民间绅士和商人的推动下,传统“公”领域呈现扩张趋势。在近代城市社会中,“公”领域的扩张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各种城镇公益事业的首次制度性整合。19世纪,处于官僚国家之外、在城市服务和社会福利中逐渐扩张的武汉地区“公”领域发展体现为地方精英群体在城市公益领域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他们建立的各种善堂、会所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并越来越主动地关注整个社会,在城市消防、治安、救生、卫生等诸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夏口一邑,人烟稠密,厥惟汉口偶一失慎,势成燎原,特置水龙,星奔扑救……前郡守刘倡率绅商,集资复置水龙,分布城镇各善、堂善局。绅商士民闻风兴起,相率举办,或独立仔肩,或由众情集腋,均能恤灾捍患,踊跃从公……”
1910年,汉口成立永济消防会,“专为研究消防,保卫治安起见。”永宁救火会由绅商“群力组合而成,以救火清道为务”。
“救生局由敦实堂创办……邑绅戚席臣、周芸青、刘步瀛、刘晋侯创议筹款造红船二艘,常年上下弋游,遇险护救”。
罗威廉认为,社仓、普济堂、育婴堂、清节堂和善堂等非官方公共机构的建立,“使地方非官僚人物逐渐增加了权力,产生了官方政策的批评者。”尽管地方绅商在“公”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仍要受到官方的制约。特别是到了新政时期,为了强化国家控制,并结束对地方绅商的依赖,政府在“公”的领域建立了许多新的机构,逐步将这些领域的控制权从个人转到政府建立的机构手中。不过,国家政权向地方绅商让渡权力的趋势并没因此而改变,相反,在辛亥革命之际,权力愈加从政府转向绅士一边去了。
清末新政,各地单独筹办新政事宜,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对地方绅商的依赖性也就随之加深。湖北1910年至1911年,军事、教育、法律、巡警、行政、自治政府、工业和铁路等新政措施年支出总数达1000万两。为解决新政中出现的财政问题,湖广总督署不得不加大课税,增加捐税名目。据报告,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期内,税收增加了1倍,从1889年的700万两到1907年的1500万两。作为新政重要措施之一的警政,开办之初也要借助于地方各种捐税和绅商的势力。张之洞受“东西洋各国警察经费,皆系出之本处民户,无论商民一律抽捐”的启示,认为本地居民生命财产“既受保卫之益,自应输保卫之资”,于是除原有保甲经费充用外,还把武昌房捐作为警察经费。收捐之法,对商民凡赁屋而居并开设店铺者,“均按房租抽十分之一,如每月租金20元即捐银元2元,余悉照此类推,业主、租客各认一半,若系自住,仍估计所值之多寡,以定抽捐之等差,至于住屋不及三间及草房棚户暨空闲暂无人赁者免捐。”张之洞还创举官捐,即所有武昌“文武署衙、书院、学堂、局所、祠庙、会馆一律纳捐,分十三等,头等月捐银圆20元,末等月捐银圆2角。如有不敷,统由本地商民劝谕筹足。”据统计,这样得到房捐共2.8万余串文。张之洞将原有保甲经费3.6万余串文充用警察经费,又从善后局借拨他项捐款5万余串文移作警察经费。这样当武昌警察总局成立后,共有约12万串文警察经费。随着湖北新政的开展,政府各种捐税负担加重,湖北商民多次向总督署请求减免整顿捐税,社会上对捐税抱怨不断,“命令下来,征集印花税和军需开支,不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在无人敢反对的一片改良的喧哗声浪中进行的。……但是大多数的新政仅是赝品,我们尽其所有的千百万钱财花掉了,却没有得到一点实际报偿。这样的新政,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面对这些情况,湖北总督衙门,在警政经费方面,只好作出让步,规定:“警察局免去小户房捐,照得省城警察局经费,抽收房捐充用,以该户房租核计,按租价十捐其一,主客各半,收取数百文以至二百文不等,历经该住户遵纪无异。”
19世纪末,各地商务总会和商团纷纷建立,成为绅商阶层日益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作用的表征。武汉地区商会也于此时建立。一开始,这些组织同官方有密切关系,受官府制约。最早建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汉口商务总局,以“开发商智、联络商情为要义”,由候补道王秉恩、程仪洛总理其事,选派“殷实诚信”,“通晓时势”之商董为总董。但商绅并不希望商会由政府控制,“汉口开办商会,早由商部立案”,“商人不甚踊跃”。
20世纪初,清政府为推行预备立宪,公布了《城乡地方自治章程》,湖北武汉地区先后成立了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研究会等官办自治机构。在此背景下,武汉地区的民间自治团体勃然兴起。从1909年2月汉口地区成立自治戒烟会起,短短两年间,汉口地区各地段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民间自治会、保安会,如汉口公益救患会、四官殿至堤口商防保安会、永宁救火社、清真自治公益会、邻济保安会、仁寿宫四段保安会、花布街商防义成社、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等。到1911年,此类组织发展到30多个,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汉口各团联合会。这些自治组织多以消防、治安、商警、卫生、慈善为主旨,其会员构成是以地方商绅为主体,包括所在区域内的城市居民,内部组织般设有正副会长、评议员、书记员、会计员、调查员、招待员、救火队长等职,由选举产生,举凡自治区域内的一切公益救患事宜均唯该组织是从,俨然是城市基层政权的雏形。政府则希望将这个联合会置于权力掌控范围之内。1911年秋,汉口成立了官商共商市政的机构——“汉口市政会”。该会由汉口警务公所科员及各区局长中选16人为议员,代表警方;以各商会总理、协理为总议董,汉口总商会议董之有学识者为议董。官商代表,每月常会2次,讨论巡警道职权内有关公益(特别是消防、卫生、道路、治安)之事。很明显,“汉口市政会”为官绅商三位一体的市政管理机构,它联络官方市政管理和民间市政管理,通“官商之邮”,显示出汉口地区市政管理机制近代化势头,同时也反映绅权的扩大,地方商绅对地方警务干预能力的增强。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湖北的警政机关解散,巡警纷纷逃亡,湖北军政府所建立的临时警察筹办处警力不足,社会秩序混乱。为此,武汉地区绅商纷纷建立保安会,维持地方治安,最终将地方治安管理权纳入自己手中。商会负责人蔡辅卿、李紫云等主持“召集商界人员,组织商团,担任巡缉土匪,保卫全市治安”,以辅警力之不足。汉阳富绅万昭度、张仁芬等,在武昌起义后,“组织商团,维持秩序,借以辅助官力所不及”。武昌商务总会会长吕逵先与柯逢时、汤化龙等发起组织武昌地方保安社,“经众人举柯逢时为总绅,设事务所二,一设山前武昌会,一设山后武昌医院,共设十一处”。武昌起义爆发,汉口“民军未即渡汉,巡警散兵力微,秩序大乱。”于是汉口各团联合会,集合汉口二十二个团体,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士绅李国镛等联名赴部呈请倡办保安社会,为防火、防盗、自卫计”,此时保安社已是“规模甫具,士民归心”,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对此评价,“照得起义以来,军务倥惚,地方治安、官绅,互相担负省垣内外保安。各社分段成立,凡有关于公共安宁之事,靡不殚精竭虑,设法维持,故人民之仓皇出走,逃窜他方,而房屋、家具赖以保存无失者,不一而足,弥莫善于户尽悬灯。募夫巡夜,以补济警察力之未遂,行之数月,无贰无虞,功效昭垂。”
综上所述,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在武汉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权力配置,官僚机器实际进行的所有官方与半官方行动中的作用已大幅度降低。一个以行会为中心、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逐步形成。绅商阶层自19世纪中后期在经济、政治领域内作用的不断提高,使绅权在1911年的政治危机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清亡后,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警政的整顿,警权统收回,警察经费由地方自筹变为政府统辖,扩大了警察职能,国家权力深入到城市社会各方面,限制了城市“精英”对警政的干预能力,商绅在武汉地区警务上的踪影也就渐渐消失。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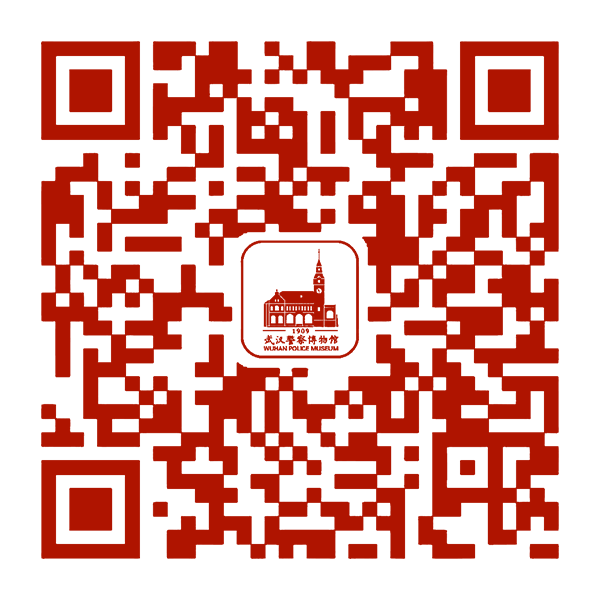
上一条:古代如何防止假币流通
下一条: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纪念章
